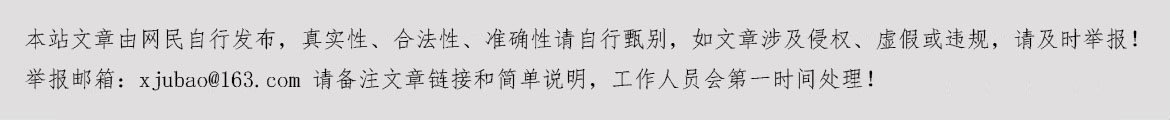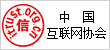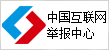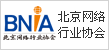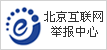宏观:今年人民币汇率应该关注什么
2022-10-16 22:56:32
摘要
今年人民币的两轮主动贬值,均与疫情密切相关。过去人民币的升贬,主要来自疫情与出口的综合作用,美元指数维持过去幅度的变化并不会构成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贬的核心因素,且过去出口对贬值幅度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未来决定人民币升贬的关键驱动,除了增量刺激政策是否出台之外,可能仍然来自疫情与出口二者。当前疫情再度肆虐与美元计出口增速的下降,短期美元兑人民币可能继续保持较大的上行压力。
今年跟随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步伐,美元指数处于节节攀升的状态。由年初的95,逐渐升至当前110的水平。所以因为美元的强势,美元兑人民币价格的上升也是正常的市场逻辑。我们需要关心的,在于人民币在美元指数上升时处于被动还是主动的贬值。主动贬值时背后的逻辑在哪里,未来这种逻辑是否强化,是否存在新的逻辑同样造成人民币大幅的主动贬值。厘清之后,首先判断主动贬值的逻辑能否延续,其次判断美元指数继续升值的空间,才能综合推测未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极限或在哪个范围。
通过对比,人民币在今年出现两轮明显的主动贬值趋势,分别在3月中旬-5月底、和7月中旬-当前。在年中人民币指数升值时,即使当时美元指数同期上涨6%以上,但美元兑人民币仅上行0.7%,即构成了对非美元货币的大幅升值。因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相对限制,美元指数的升值对人民币的被动影响,远小于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应的货币。
今年两轮的贬值周期,基本与疫情对经济权重地区的影响问题高度相关。例如3-6月国内深圳、上海、北京先后经历了疫情的冲击;而7月以来在用好存量的基调之下,当前国内又面临BA.2和BA.5新变种的冲击。疫情防控所衍生的消费下行、供应链阻断、信心缺失等问题,构成了天然抛售人民币的基本面压力。
所以以中美十年期国债的利差,是反应今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同步指标,背后蕴含着对中美长期经济展望的差异。它与汇率并不构成明显的先后或完美的节奏匹配,但是长期方向的趋同以及利差价位幅度的罕见,能够指引当前市场对汇率方向的判断,以及贬值压力的暗示。
今年中美利差的剧烈走贬,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联储加息背后的美国经济韧性底气,另一部分则是国内防疫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二者分化在利差中得到剧烈反应,中美利差已达到了2008-2010的极值水平。挑战在于当前的汇率波动相对2008年更为自由,这给予了美元兑人民币更大的上升压力。
从资金维度看,自2020年疫情首次冲击之后,央行结售汇差额稳定维持较大的正值区间,即长期构成了人民币相对外币供小于求的格局,这与2020年以后人民币持续走强的逻辑相印证。但是进入2022年,资金流入相对减小,不足以解释当前人民币已出现较大的贬值幅度。但如果结合外贸出口金额持续的超预期,即比对结售汇差额中代客项目,可以清晰发现银行自身项目的大幅流出。所以外贸的超预期,构成了当下如此极端的利差环境下,人民币贬值幅度得以对冲减缓的存在。
所以未来如何评判美元兑人民币,实际上参考6月美元大涨下美元兑人民币仍然稳健的行情,只要国内基本面得以稳住,则美元升值并不会构成贬值的核心因素。真正的核心在于疫情与出口两个维度。如果疫情持续在四季度对国内构成困扰,人民币可能仍然承受压力,7.0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关口,但出口的韧性能够继续延续相对其他弱势货币更缓的贬值幅度。然而风险在于出口一旦出现下滑,则疫情下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可能存在进一步放大的风险。这是相对于猜测美元指数如何走,判断人民币走向时我们更需关注的因素。
(文章来源:中粮期货)
文章来源:中粮期货